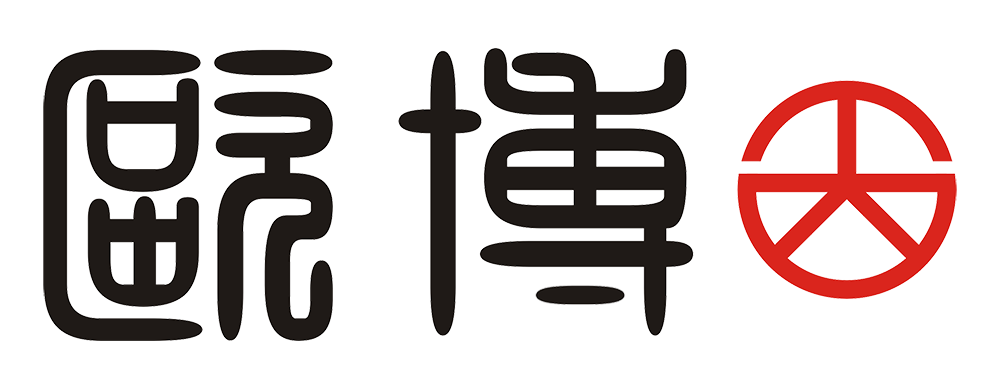講到現代管理,我們腦海中自然會冒出兩個字:“制度”。的確,制度化管理是現代化管理的特征。我們在企業里面看到的ISO體系、考核體系、ERP系統等等,都可以說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主要形式,他們都是由一系列的流程、規定、表單所構成,這就是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企業家都特別重視企業的制度建設,各種各樣的流程文件、規章制度充斥著企業,但效果卻很不理想:一方面執行力很差,另一方面制度也沒帶來企業真正的規范化和效益的提升。制度很多,但卻沒用,成了很多企業的現狀。很多人分析這種現狀時,把它歸因于國人的國民性,或者歸因于員工的職業素養,或者歸因于老板們不懂管理。

總之,我們認為制度化管理在西方行得通,在我們中國的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遇到了問題是執行力不夠造成的,強化執行往往是這些專家給出的解決方案。他們從沒有懷疑過現代管理是否就真的只是“制度化”這三個字這么簡單?沒有審視過西方的制度化管理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自然也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我們看一個西方管理當中非企業化的例子:我們在各種電影、電視作品中都能經常看到法庭審案的情景,我們腦海中比較容易聯想到的是律師、法官、公訴人等等這樣的角色,因為他們淵博的法律知識和雄辯的口才以及超常的智慧,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的表現簡直把法庭當成了展現他們才華的舞臺,這就是西方的法庭判案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

由此,我們會得出結論:龐大的法律知識體系和掌握這些知識的相關專業人才是構成現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因為是這些東西在主宰著司法實踐。
很多的企業家對自己的企業管理也做了類似的理解。所以,他們特別重視制度條文的制定和專業人才的引進,這使得我們的管理越來越走向專業化、精英化的軌道。但效果怎樣呢?只能說差強人意。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制度化建設的根本和靈魂所在。

回到我們所講的法庭判案當中來。當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專業的法律人士律師、法官、公訴人身上的時候,甚至認為法庭判案就是這些專業人士間的游戲的時候,我們忽視了法庭中最重要的一群人,這些人并不需要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也不需要特殊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我們只能把他們稱之為一群普通人,但他們其實決定著法庭真正的結果,他們的名字叫“陪審團”。
只有當他們裁定被告有罪時,法庭的專業人士以及他們的專業知識,才能開始真正起作用。而在這之前,法庭控辯雙方,包括法官在內,這些專業人士的工作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所有與案件相關的事實,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出來。這一過程并不是法律條文起作用的領域,而是證據的收集和呈現起到關鍵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一階段所有專業人士的工作都在為非專業人士服務,他們千方百計地把有利于自己這一方的事實挖掘出來,呈現在陪審團面前。讓陪審團去作出有罪或無罪的裁決。

而陪審團憑什么作出裁決呢?不是專業的法律知識,因為大多數陪審員們并不具備這些知識;也不是專業的法律才干,因為大多數陪審員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現代司法制度為何要做出如此荒誕的設計呢?要讓一批并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的人來決定人的生死和案件的最終結局,卻讓那些具備相關知識和能力的專業人員來為他們服務呢?
這只能說明現代司法制度的設計者們在這里進行了一個用心良苦的設計,這個設計的核心就是一切的制度設計必須以人的良知為核心和基礎。只有當良知作出裁決以后,專業的法律知識才開始有效運作。因為那些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的陪審員們,除了憑人人都有的良知面對事實作出評判以外,他們無所依托。當然,前提是呈現在他們良知面前的事實必須是真相,并且是所有人憑良知就能判斷是非的真相。而這就是陪審團作出決定之前,整個法庭所進行的工作。

控辯雙方的律師只是在引導著這些事實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呈現。他們比的并不是各自掌握的法律條文,這里面的確有技巧和能力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并不體現為雙方法律知識的多與寡,而是對這些事情的引導和收集事實的能力。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制度設計者們對人的良知的信任,遠遠超過對人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知識的信任。也就是說,現代司法制度歸根結底是建立在良知基礎之上的。無論這一制度在各國的實踐以及它在實際當中的應用如何,這一制度的設計本身都無可爭辯地證明了“良知是制度的基礎和核心”這一原則。

現代司法制度是如此,現代企業制度又怎么可能違背這一原則呢?關乎到人的生命的事情良知都高于制度,關乎到人的生活的事情,制度怎么可能替代良知呢?
所以,如果說我們很多的企業面臨制度落地的困局,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無視制度化建設的基礎是人的良知這一事實。

不能喚醒人的良知,制度背離了良知,當制度出現困境的時候,良知不能起作用,這些是所有制度難以落地的根本。什么時候當我們的企業遇到重大的問題,先由良知說了算,再由制度說了算的時候,企業的管理就會好辦很多。這樣的制度必然不會違背良知,而只能為人的良知服務,成為良知起作用的一個工具而已。說到底,就是只有當一個企業的制度是以人的成長為目的的時候,這樣的制度才是有用的。
現在很多企業在管理的思維上都已經樹立起了把企業視為員工成長平臺的概念,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為我們終于明白了,所有的制度說到底都是為人服務的。“人是目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

所以,千萬不要認為西方管理思想現在只講制度、不講良知了,對良知的認知和肯定一直是人類東西方思想家們共同的理念。中國人的老祖宗孔孟對此有諸多的論述。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講的就是良知人人生而有之;孟子提出“不慮而知,謂之良知。”以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同樣認為良知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識”,與中國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提出的“良知即天理”不謀而合,他們都同樣認為天地萬物的“理”存乎于人的內心。我們內心的良知和美德與天地萬物的道理和知識相通,這是我們人能夠認知天地萬物的根源所在,正因為如此,我們人才可憑良知對事物的是非進行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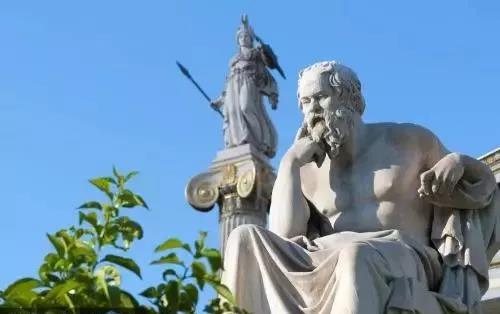
英國學者羅伯特·艾倫在其《哲學的盛宴》一書中寫道:“蘇格拉底曾說,人們的內心深處有一個精靈,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他都在觀望著,每當我們想做壞事的時候,良知的精靈就會跳出來阻止我們對我們說‘不可以’,但若這是一件該做的事情,精靈不會做出任何舉動,良心的譴責,會讓我們對錯的行為不安和不忍。”
羅伯特·艾倫在該書中還提到了另外一位對人類現代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思想。笛卡爾在《哲學原理》一書中提出了人的“天賦知識”的概念。羅伯特·艾倫對“天賦知識”的解讀是:“不需要通過經驗存于人心的知識,并且是正確判斷、辨別真假的能力。”笛卡爾提出的“天賦知識”和孔子提出的“生而知之”,都是在講人人與生俱來的辨別力和判斷力,孟子稱其為良知、良能,也就是蘇格拉底所認為的人內心深處的精靈。

可見,東西方思想家,古代、近代的先哲們對人心靈的認知是相同的,他們都認為人的內心先天存在著對事物進行是非判斷的能力,這就是人的良知。這個良知不是后天獲得的,與外界無關,與后天的知識無關。這是他們對人性的基本信賴,這份信賴也是現代管理制度設計的指導思想。
所以,文明的發展方向是以良知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和完善,并且以人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