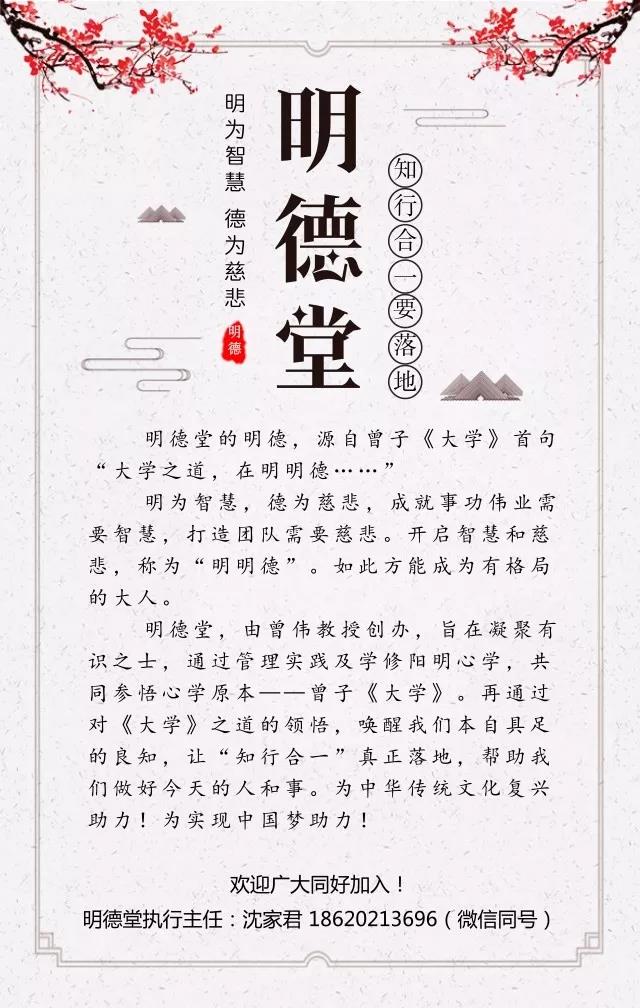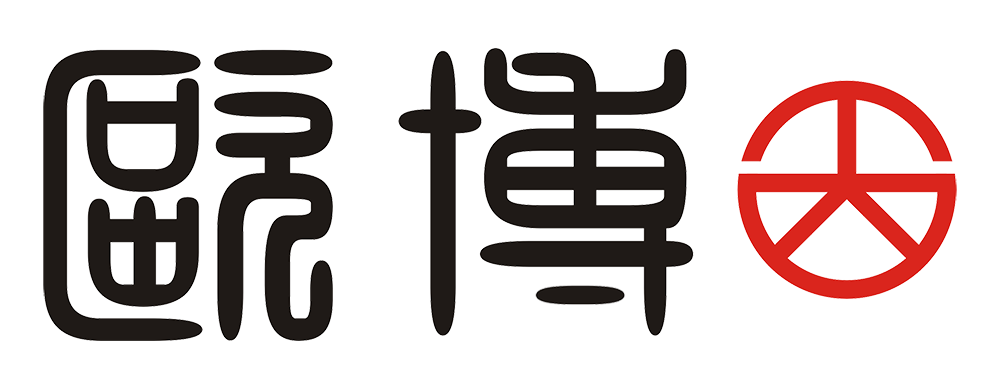下文出自曾偉教授根據領導力課程系統整理出來的新書《知行合一要落地》,我們將連續推出。該書是結合管理實踐,對陽明心學和曾子《大學》的解悟。

《大學》說“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靜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認為靜就是安靜。既然是安靜,為什么后面還要搞一個“安”字呢?
孔孟那個時代離甲骨文時代不遠,那時候靜、安是什么意思,大家還能夠明白,但漢文字經過這么多年的演變,很多字的本身的意思我們已經看不出了,它們的意思已約定俗成,它們原來的意思我們都逐漸遺忘了。
我們看一下“靜”的金文。
 ?“靜”字的金文大篆
?“靜”字的金文大篆
“靜”字沒有甲骨文,我們找到了“靜”字的金文。金文和甲骨文同時代。 “靜”的金文的右邊是甲骨文的另外一個字:爭。甲骨文的“爭”字是什么形狀呢?是一個人的左右手往相反方向用力,在使勁地擰著一個東西。我們洗完衣服、被單都要擰一下,有時一個人擰不了,還要兩個人幫忙擰。擰衣服、被單的時候,我們的雙手是一個向左用力,一個向右用力;一個是逆時針,一個是順時針。我們的雙手向相反的方向用力,衣服、被單就被我們擰干了。

本來“靜”是很安靜的一個字,為什么在它的右邊搞一個“爭”字?“靜”是安靜。都安靜了,都沉靜了,都啥事沒有了,怎么還要搞爭?“爭”意味著什么?
“靜”不是啥事都沒有。“靜”是兩個完全相反的力量在使勁糾結,在博弈。這種狀態企業里面有沒有?在變革最激烈的時候,企業的人身上就有兩股相反的力量在糾結,他們在改與不改、在前進與后退、在支持與反對間糾結,在良知和習性間糾結。
《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知以后你知道該怎么做,但你同時又有妄念,我們要把妄念止住,按照自己的職責要求去做,這叫定。但是讓每個人都按自己的職責要求去做,他是不是很舒服?不是。

企業把規定定出來,把制度定出來,員工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干,然后就老老實實、歡天喜地去干了?不是。企業的規定、制度會跟他內心的習慣沖突,每個人都想隨心所欲,都想按自己的意思辦,企業給他定了那么多條條框框,他高不高興?不高興。所以,職責要求是一回事,他內心能不能完全遵守又是一回事。這時候他就開始矛盾了,表面上他平安無事,但是他的內心中波瀾起伏,這個矛盾直至平息的過程就稱之為靜。
宋朝儒學大師周敦頤說過一句話:“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一張桌子,它動就是動,不動就是不動。它不會動里有不動,不動里有動,物體就是這樣。但神不是這樣,神是動里面有不動,靜里面有不靜。

所以,人都是“神”。企業里面做變革,人們表面上若無其事,心里頭波瀾壯闊;表面上舉手同意,骨子里堅決不做。你還奈何不了他。為什么?他此時都已經超越人的概念,他“神”了。所以,我們做管理不僅僅跟人打交道,還跟“神”打交道。
企業里面有好多神,有時候各路神仙、各路諸侯搞得你焦頭爛額,所以企業不好管,因為你管的是神。神有什么特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企業里面的好多人就是這樣,你說他動了,他又沒動;你說他靜了,他又不靜。他永遠在矛盾狀態,你不知道怎么辦,這個過程要持續很久。

所以,是不是定了以后就完事了?不是。好多企業都搞制度,制度的目的就是定,就是讓每個人定下來,讓這個人知道他該干什么,讓那個人知道他該干什么,然后每個人按規定去做。這似乎很簡單,但是《大學》里面講得很清楚,定了以后有一段“神”的過程。定的是人,但人立馬變成神,他立馬就神了,他的神通馬上就來了。你定什么他都有辦法對付你:表面上他不反對你,實際上他又不聽從你,這個過程要持續很久,這就叫靜。
所以,我們搞個制度就行了嗎?搞制度最后把人變成了神,不搞制度他還只是人,他有什么是什么,只是隨心所欲。而一搞制度,他為了對付你,立馬變得不是人,而是神。這個神的階段是個必經的階段。神到最后是什么呢?神到最后就成圣了。
到了圣就是孔子所講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時他做什么都能遵從規矩,而又不違反他的內心。所以,“神”是一個中間階段,只要我們一直堅持,制度一直堅持,他還能一直神下去嗎?不會,他會放下糾結,進入真正的靜的狀態,并且從靜走向安。
所以,靜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故事都在這里發生,這時候我們能不能堅持、能不能持續非常重要。
靜是一個由不靜到靜的過程。這個過程結束了,人們的私欲放下了,最后才能達到老子在《道德經》里講的“不欲以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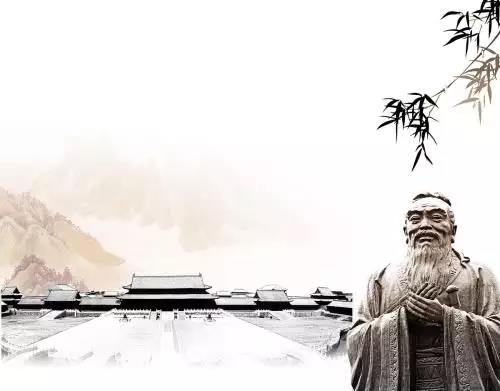
“定”是拿社會關系約束人。我們用制度約束員工,員工會糾結,但他會不會一直糾結?不會。推一個制度下去,員工一開始會問:我為什么要服從?我為什么要遵守這個規定??我憑什么要遵守這個制度?我憑什么按你的做?他的心里總有很多“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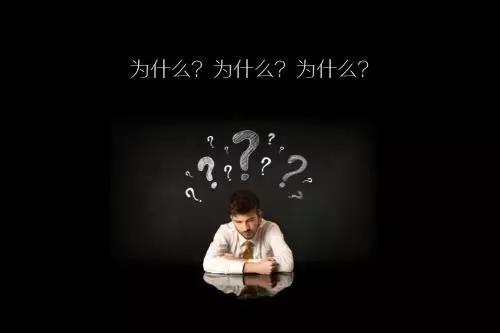
其實,制度是回答“為什么”還是回答“是什么”?制度回答“是什么”,制度告訴你該怎么做,但是我們人一定要問“為什么”。
所以,“靜”是你的“是什么”出來了,馬上他的“為什么”也出來了,兩股力量擰巴著。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暗流涌動,硬對抗、軟對抗都有,糾結得不得了。因為他的內心老問“為什么?”、“憑什么?”,總要找理由。如果我們一直堅持,最后他會放下“為什么”,就只管“是什么”了。因為他覺得反正搞來搞去也沒用,除非自己離開。放下了“為什么”,人就安了。
人不要老在“為什么”上糾結,“為什么”問多了,人心里無法得安。
只要一個人問“為什么”,就會有一個對和錯的問題。等你把答案給到他,他馬上又開始懷疑:難道真的對?會不會搞錯?

買雞蛋的時候,你一眼看到一個大個的,但當你把它拿到手里,你又發現它不是最大的,于是你把它放回去,又拿一個大的。可這一個拿到手里,你一看又不是最大的,你挑來選去,最后就搞不清哪個大、哪個小了。為什么你搞不清哪個大哪個小?因為你總是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心總不定。
所以,人不要老在對錯上糾結,因為一切的對錯來源于行動,來源于你去做。放棄就一定錯,堅持往往就對。老執著于對錯,就會舉棋不定,就會六神無主。你只有經常橫下一條心:做!管它是對還是錯,吃這碗飯就認這個命。
不管遇到什么事,老想“為什么”,人的心不可能靜。不靜就會不安,不定就會不靜,所以最重要的是早點讓自己的心定下來——管它對錯,逮著一個先做。想來想去,只會越想越不對,最終就不做了。
不要助長自己的不安,不要助長自己的猜疑,不要助長自己的多變。總是猜疑,總是不安,總是多變,養成習慣,受傷害的是自己。所以,就要橫下一條心,不管對錯,先做了再說,然后堅持去做。堅持到底是唯一法寶。
真把企業搞下來的就是那些一直咬著牙堅持做的。咬著牙說明什么?說明他已經不問“為什么”,他只管“是什么”。他覺得:有什么理由問“為什么”?誰叫我攤上這些事?誰叫我干老板了呢?死都要死在這個地方,只能硬著頭皮上。最終成功了。
靜就是努力克服自己私欲的階段。